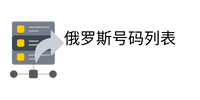法律意义上的归因必须与技术意义上的归因区分开来,尽管后者构成了前者的事实谓词。从法律上讲,归因的概念表示将人类行为视为国家行为的情况。将干扰选举的网络行动归咎于国家最明确的依据是,该行动是由该国的一个机关进行的(《阿塞拜疆安全法》,第 4 条),就像俄罗斯 GRU 2016 年干预美国大选的案例一样。一个实体可以通过在国家法律中被指定为国家机关,或者通过“完全依赖”国家运作而成为国家机关。后一种依据排除了国家通过一个在国内法下不具有法定机关地位但却为国家并在国家指示下从事网络活动的组织(换句话说,事实上充当国家机关)来逃避选举干预责任的可能性。
最有可能的归因依据是其
按照国家指示、指挥或控制”行事(《反网络攻击法》,第8条)。这似乎是将互联网研究机构2016年的行动归咎于俄罗斯的法律依据。
指示、指挥和控制这些术语相当模糊。有些情况很明确,例如,一方面,国家与进 Viber 手机数据 行选举干预的营销机构或社交媒体咨询公司等私营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满足第8条标准);另一方面,“爱国黑客”在没有任何国家参与的情况下开展行动(不符合第8条标准)。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评估非国家行为者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否构成指示、指挥或控制并非易事。这不一定是因为归因规则的运作缺乏明确性,而是因为缺乏关于国家与非国家行为者之间关系性质的证据。
非国家行为体对选举进行的网络干预
若未归咎于国家,则不违反国际法,尽管它可能引发下文将要讨论 哪些工作不需要数学? 的积极预防义务。即使可归咎于国家,干预也必须违反对选举实施国承担的义务,才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在这方面,讨论首先转向禁止干预。
禁止干预
在外国网络选举干预方面,最受关注的国际法规则是禁止干涉其他国 海地名单 家的内政或外交事务(见《塔林手册》第 66 条)。该规则出现在 1970 年《友好关系宣言》等文书中,是一条被广泛接受的国际法规则,其在网络空间的适用性已由 2015 年联合国政府专家组报告确认,该报告随后得到大会的认可。该规则的变体也出现在《美洲当非国家行为者 国家组织宪章》等条约中,但在应用这些规则时应谨慎,因为它们的参数可能与下文讨论的习惯规则不同。